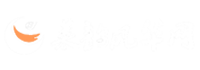- 莱州市光州东街678号 13583595082
- fdliang87@126.com
乡土乡音
欢迎您阅读:六月十九: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庙会
六月十九: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庙会
过西这地方,在莱州地面上算是个有说头的古镇。老辈人讲,这名字都带着典故 —— 过国之西,寒浞居子的封地,最早是方、国两姓立的村。单说这庙会,一年就有五个,在周边十里八乡都数得着,而最让人惦记的,还得是六月十九那一场。
 我的家乡过西在这里
我的家乡过西在这里
咱这地方把赶庙会叫 “过庙”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会儿,这可是比过年还让孩子盼的事儿。头半个月,村里的孩子就开始扳着指头数日子,路上碰见了,三句话不离 “快过庙了”。大人们也早早就忙开了,妇女们盘算着蒸几锅新麦馒头,男人们则琢磨着请哪些亲戚,就连平日里最抠门的大爷,也会多割二斤肉,说要让孩子们解解馋。
 盼望着过庙的孩子们
盼望着过庙的孩子们
头着过庙的一两天,家家户户都要打发人,往远近的亲戚家跑,挨户去请:“他婶子,他大爷,六月十九一定来俺家过庙啊!” 记得那年我十三岁,家里让我去七里外的徐家村请老姑。老姑膝下没有儿子,见着娘家来的重侄,老远就迎了出来,拉着我的手不放,脸上的褶子都笑成了花,两眼眯成一条线:“哎哟,俺家大孙子来了,快进屋,姑给你找糖吃!” 第二天一早,她就让外甥用独轮车把她送到了我家。一进院门,看见我爹 —— 她的侄子,还有我们三个重侄,老姑的嘴就没合上过,拉着我们挨个打量,一个劲念叨:“都长这么高了,好,真好!” 那几天,她总爱坐在炕头上,给我们讲家里的老故事:爷爷年轻时怎么在地里刨食,奶奶怎么教小辈做人,哪家亲戚在困难时帮过咱,哪家孩子懂事有出息。那些家史、家风,还有扯不断的亲情脉络,像串珠子似的,被她娓娓道来。老姑在俺家住了五天,闲不住的她,还拉着我去串了好几家老亲戚,在炕头上喝着粗瓷碗里的茶水,说不完的贴心话,把夏日里的欢喜掰成了一瓣一瓣的,分给了每一个人。
 亲戚们相见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
亲戚们相见总有说不完的心里话
最让孩子们疯魔的是唱戏。过西大队的院子里,早早就搭起了戏台。县里的京剧团、吕剧团一来,演员们在后台吊嗓子,孩子们就扒着戏台缝往里瞅,看那花脸的油彩怎么涂,水袖怎么甩。开戏时,黑压压的人坐满了院子,连墙头上都趴着半大孩子。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一亮相,台下叫好声能掀翻屋顶;吕剧《姊妹易嫁》演到动情处,前排的老奶奶们抹着眼泪说:“这闺女,心眼实诚。” 白天日头毒,大人们摇着蒲扇看戏,孩子们就钻到戏台底下乘凉,闻着后台飘来的胭脂香,心里美极了。
 戏园子里挤满了看戏的大人和小孩
戏园子里挤满了看戏的大人和小孩
这六月十九庙为啥比别的庙更热闹?老辈人说有三宗巧。头一巧是麦收刚过,新麦子磨的面白得晃眼,蒸出的馒头暄软香甜,咬一口能尝到阳光的味道。家家户户的锅灶从早到晚不闲着,菜锅里炖着豆角土豆,飘着肉香,连胡同里的狗都比平时欢实,围着灶台转圈圈——人们要借此欢庆刚刚的丰收。
 新麦蒸的白馒头是劳动成果的享受
新麦蒸的白馒头是劳动成果的享受
二是农闲正好赶上手头宽绰。玉米长过膝盖,地里的活计松快了,队里分了钱,大人们就盘算着扯块花布。供销社的布摊前永远挤满了人,姑娘们挑着粉红的、湖蓝的的确良,比划着做件新褂子;老太太们则选藏青的粗布,说要给孙子做条结实的裤子。孩子们最盼的是三分钱一根的冰棍,攥在手里舍不得咬,看着冰棍慢慢化成水,滴在手背上凉丝丝的。
 1972年生产队里开资的快乐场面(莱州档案资料)
1972年生产队里开资的快乐场面(莱州档案资料)
三是瓜果正当时。吴家庄子的甜臊瓜带着股特别的香,咬一口脆生生的;西瓜摊前,卖瓜的老汉用指甲盖 “啪” 地划开瓜皮,红瓤黑籽透着沙甜。还有那 “立猛水”,土法熬的山楂汁装在玻璃瓶子里,喝一口酸得眯眼睛,却比啥汽水都解渴。六月十八下午,卖瓜的商贩就推着独轮车来了,在街两旁占好地盘,夜里就裹着麻袋睡在车旁,生怕被别人占了好位置。
正日子那天,过西的街上挤得挪不动脚。卖针头线脑的、捏糖人的、耍猴的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耍猴的敲着锣,猴子穿着红坎肩作揖,孩子们扔过去半截冰棍,猴子接过来就往嘴里塞,逗得人哈哈大笑。最挤的是卖西瓜的地方,老汉们切开的西瓜摆成小山,红瓤映着日头,看着就解渴。有那精明的小贩,把西瓜切成小块,用竹签插着卖,一分钱一块,孩子们攥着皱巴巴的分币,吃得满脸汁水。
 大街上赶庙的人摩肩接踵
大街上赶庙的人摩肩接踵
如今再回想起过西的六月十九庙,鼻子还能闻到新麦馒头的香,耳朵里仿佛还响着戏台的锣鼓。那些年的热闹,是麦收后的踏实,是亲戚相聚的暖,是孩子们眼里的光。现在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可总觉得少了点啥 —— 或许是那口带着烟火气的乡情,或许是庙会上那股子热热闹闹的人间滋味。这乡土乡音啊,就像老槐树的根,深深扎在心里,无论走多远,一想起,就觉得浑身暖和。
 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对乡土乡音的无限思念
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对乡土乡音的无限思念
——《莱韵风华网•快乐生活•乡土乡音》栏目组编辑
文章点评